第二十章:執政者對危機的反應
原书及其作者:《墓碑——中國六十年代大饑荒紀實(下篇)》,楊繼繩,天地圖書第七版。
系列上一篇:五风
-----
>p804 任何一個政府,面對危機都會採取相應的對策。中國共產黨及其所領導的政府面對全國性的大饑荒,也曾調整政策,糾正錯誤。這主要在1958年11月到1959年7月廬山會議之間的八個月。
毛澤東的一切糾偏措施以不傷及「三面紅旗」為限,而「三面紅旗」恰恰是大饑荒的直接原因。…… 在廬山會議以後,連這個限度以內的糾正措施也廢除了。1960年又一次大躍進,又一次共產風,1961年又一次糾偏,但為時已晚,大饑荒持續了三、四年。
一、糾偏只有八個月,廬山會議一風吹
这一章里作者仔细的概括梳理每个会议做了什么,史料价值很扎实。
一开始,1958年11月到1959年7月之间的许多会议上,毛泽东带头做了一些回归事实,向农民让步的调整,但是同时也始终坚持着“三面红旗”的基本说法,比如提出“(成绩和问题的比例是)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关系”就是一个缩影。
到了1959年7月,庐山会议先让大家各说问题,后半场就开始批人反右倾,所有对农民让步的政策一落到具体措施层面,就被报告为“一股右倾歪风”,随即一切调整措施都被推翻,变为了反右倾运动。
>p807 反右傾以後的1960年又是堅持大躍進方針的一年,這一年餓死人最多。1961年1月,八屆九中全會又決定對國民經濟實行「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方針,從大躍進中退回來。但是,在中國當時那種政治制度下,身處中央的決策者們很難得到下面的真實情況,他們發現問題總是要晚幾個月,而且他們知道的危機狀況比實際情況要輕得多。糾錯過程又和反右傾交叉,反右傾不僅阻礙糾錯,還助長錯誤。所以,中國共產黨雖然努力糾正錯誤,但大饑荒還是持續了三、四年。
二、毛澤東獨自「唱低調」,別人還得唱高調
>p809 但是,這樣的話只有毛澤東能說,別人說了就有右傾之嫌。所以,這些比較接近實際情況的話都是毛澤東先說出來。毛澤東說出了這些話,又被他的下級奉為「先知」、英明。由於批評反冒進、反右派等殘酷鬥爭,在各級幹部頭腦中留下了深刻印象,雖然毛澤東說了這些話,也沒人敢付之實踐,還得繼續唱高調。…… 大家都知道毛澤東對「三面紅旗」情有獨鍾,對「群眾運動」倍加愛護,大家都知道這是毛澤東的基調。現在毛澤東低調講話,大家看作是暫時的,不是根本的。何況毛澤東在講這些低調的話時,還講了另一面的話。報紙上還成天在歌頌大躍進和人民公社。所以,毛澤東雖然說了一些實事求是的話,下面也不敢真正落實。
>p810-811 毛澤東感到他的意見難以落實,就把糾正偏差的想法一竿子插到底,直接把他的想法告訴到生產小隊一級幹部。1959年4月29日,毛澤東以「黨内通信」的形式,致信給「省級、地級、縣級、社級、隊級、小隊級的同志們」,說「我想和你們商量幾個問題」。…… 毛澤東深知,底層幹部和農民與上層統治者的矛盾是很深的。他的常用手法是,越過中上層幹部,直接向底層發佈他的意見,有時直接發動底層。這封信如此,以後的文化大革命更是如此。這樣造成的印象是:毛主席是英明的,事情就是各級幹部搞壞的。
三、所有制上退讓,但不能否定「一大二公」
>p815 在糾正大躍進的偏差中,幹部們頭上一直有一把懸劍,罪名有的是:右傾機會主義、觀潮派、算賬派、地主、富農、反革命分子、壞分子。這一把懸劍使人們寧左勿右,阻礙着有限的糾錯政策的落實。
- 这不是小心就能避免的问题,集权体制的一切都浮在人身依附和最高领导人想法上,没有具约束力的规章制度,躲过了大跃进的潮起潮落,后面还有一系列的政治运动能让最高领袖想整谁就整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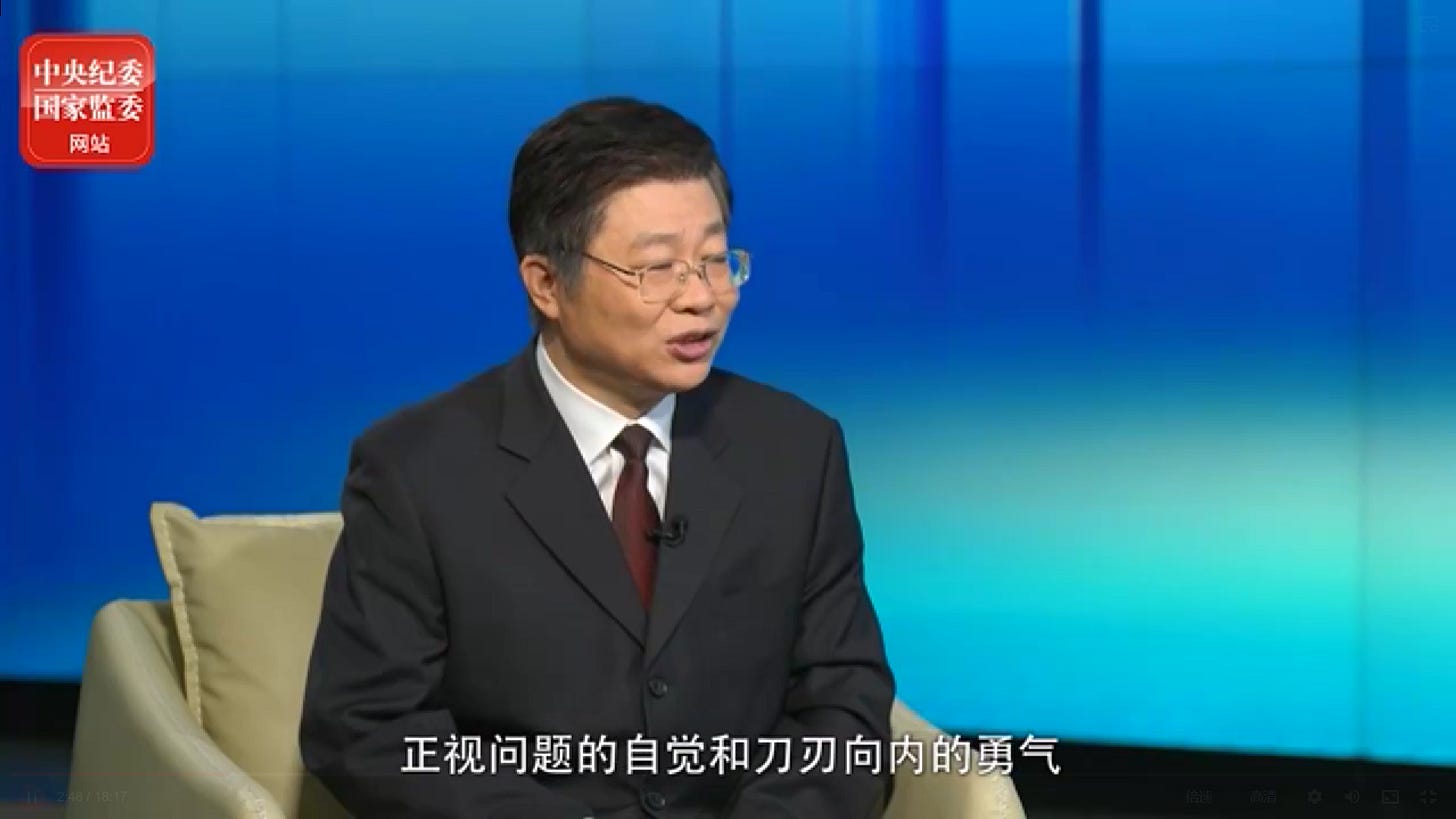 |
四、搞退賠,僅是紙上文章
>p816 農民的房子已經拆了,重建是很困難的,拿走的東西大部分都揮霍了,退賠很不容易。由於中共中央多次督促,各地報上來不少公社退還給生產隊、生產隊退還給農民的數字。
這些數字大部分是虛誇的。
- 毕竟这些让步不是百姓自己挣来的权利,是统治者的恩典,一旦发现退赔救灾如此困难,一清算发现救百姓的粮食需求如此之大,账上的缺口变得如此显眼——地方落实不力,中央的恩典也很快收回,还要恼羞成怒的开始反瞒产、反右倾。
- 大部分农民很好满足,只要拿回一点原有利益就感恩戴德。
五、擴大農民自由,但執行中遇到意識形態障礙
>p818 集體組織不能保證農民的生活,只好給社員一點自由,讓他們自找生路。從1959年春夏之交開始,對農民的某些政策開始鬆綁。
>p820 實際上,有些地區並沒有按中央5%的要求給足自留地。江蘇省全省平均只佔4.7%,有的地方不足4%。一部份幹部認為自留地和自由市場「是資本主義」,怕影響集體生產,怕社員搞「自發」,對於恢復自留地的規定採取陽奉陰違的態度。四川省根本沒有執行中央關於自留地的指示。
六、實行責任田,僅是暫時措施
>p820 在農業集體化以後,農村實行生產資料公有、集體勞動、統一經營、統一分配的原則。怎麼分配?按工分分配。工分掙得越多,分得的勞動報酬就越多。開始是「死分死記」,壯勞動力勞動一天記12分,普通勞動力勞動一天記10分,婦女和兒童勞動按勞動能力不同,一天記5分或6分不等。但「死分死記」的辦法造成出工不出力。後來又發展為「死分活評」。每天勞動以後,晚上開會評工分。但評工分時拉不開面子,很難評出真正的勞動成果。後來又發展為「定額包工」的辦法。這一畝地交給你鋤,鋤完了,再檢查一下,如果合格,就給你30分。從包工發展到包產到組,最後發展到包產到戶。所謂包產到戶,就是這塊地包給一個家庭,上交集體1,000斤,多餘的歸自己。責任越明確,勞動和分配掛鈎越緊密,勞動積極性就越高。包產到戶也叫「責任田」。但是,包產到戶主要生產過程是家庭經營,打破了集體經濟統一經營、集體勞動、統一分配的原則,因而被認為瓦解集體經濟、走資本主義道路。
>p822 在三年大饑荒中,挽救危機最有效的辦法就是包產到戶。如果沒有這項措施,可能還要餓死更多的人。但是,對這群眾的自發的救命措施,省、縣級領導人只能採取「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的態度。只有安徽的曾希聖1961年才明確支持並推廣,不過,曾希聖也是採取明修栈道,暗渡陳倉的辦法,對外稱「包工包產責任制」,實際搞的是「包產到戶」。毛澤東和中共中央對包產到戶的態度微妙而多變。在1959年,由於毛澤東和中共中央對饑荒嚴重程度估計不足,對剛露頭的包產到戶極力打壓。
七、下放城鎮職工,減輕糧食壓力
>p825-826 糧食徵購是為了滿足城鎮的需要。工業上得太快,城鎮人口增長太快,使農業不堪重負。陳雲說,三年來招收職工2,500多萬人,使城市人口增加到1億3千萬,現在看來,並不恰當。大躍進中,各地上的工業項目太多,造成物資、財政十分緊張。因此,「下馬」一些工業建設項目,精簡城鎮人口,是解決糧食不足和緩解緊張氣氛的一個必要措施。陳雲對此作過精確的計算,他說,下鄉1,000萬人可以少供應糧食45億斤,下鄉2,000萬人就可以少供應糧食90億斤。
在大躍進中,由於要盡快地建立獨立的工業體系,大批農民進城當了工人,成了吃商品糧的人。他們由農民身份變成了工人身份,他們的社會地位上升。但是好景不長,糧食一緊張,他們就成了精簡下放的對象,又由工人變成了農民,社會地位下降。
八、整風整社,把責任推給基層幹部
>p828 上述糾錯措施,僅僅是針對「三面紅旗」中過激的問題,事實上正是「三面紅旗」造成了大饑荒。所以,一糾錯,就會傷及「三面紅旗」,一傷及「三面紅旗」,就觸動了毛澤東等人最敏感的神經,認為有一股「猖狂的反對社會主義道路的逆流」。認為大量餓死農民的原因不是「三面紅旗」,而是「猖狂的反對社會主義道路的逆流」。
「猖狂的反對社會主義道路的逆流」來自何方?毛澤東認為,在上層來自右傾機會主義分子。而在基層則來自地、富、反、壞、右。他們反對「三面紅旗」,是他們造成了農村的嚴重問題。自從1960年底信陽事件在黨的高層揭露以後,毛澤東就把過去九分之一(「一個指頭」)的問題改為「三分之一」的地方有問題。而這三分之一的問題是基層幹部中壞人掌權造成的。這就把農民受摧殘的原因歸罪於基層幹部。
>p830 因此,一些餓死人較多的地方,都進行民主革命補課,就是像土地改革時期那樣,像鬥爭地主惡霸一樣鬥爭基層幹部,讓農下中農申冤訴苦,然後全面奪權。
>p831 中國農村的基層幹部中,的確有一批流氓地痞,他們借助國家政權,狐假虎威,欺壓百姓。但其中多數人是在執行了中共中央的政策時才傷害了農民。有些人在執行中過激了些,才對農民造成了更嚴重的傷害。這中間雖然有幹部素質低下的原因,但其責任應在中央,而不能讓一些基層幹部當替罪羊。
九、幾個重大錯誤一直堅持到底
>p831 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共中央雖然在所有制問題上一波三折地調整極左政策,也曾下令糾正農村幹部作風,改變1958年大躍進中一些過激的做法,但是,在幾個重大的問題上,沒有採取切實措施。這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在糧食問題上對農民見死不救,繼續高徵購,繼續出口,從而加劇了饑荒;二是在建設速度和經濟指標上,繼續堅持大躍進,遲遲得不到調整。
>p839 現在回過頭來看,對挽回危局起重要作用的是自留地、自由市場和責任田。但這些是中共中央在很不情願的情況下,做出的無奈的選擇。而自留地、責任田中的大多數是農民背着政府做的,縣以下幹部睜一隻眼閉一隻眼,中央和省級不知道搞責任田的面有這麼廣。從1958年過激政策退回去(所有制,高指標)是形勢所迫,但對阻止形勢進一步惡化起了作用。在這期間,中共中央所做的事就是反右傾。 這場政治鬥爭,加劇了災難。
-----
原书信息:楊繼繩,2008,《墓碑——中國六十年代大饑荒紀實》。天地圖書,第七版,ISBN 978-988-211-908-6
评论
发表评论